(第五章/1)买椟还珠
“归根到底人类社会尝试过的所有制度都只不过是那个装珍珠的盒子,自由才是里面那颗珍珠,问题是我们越来越热衷于把盒子造得精美,却遗忘了里面的珍珠。”
――罗叔卡博《盒子变迁史》
正当我连续逃课整天窝在宿舍钻研百家乐快要走火入魔时,文学院行政处一个负责此次港澳旅行游后感的收集和评审工作的团委老师托人传话说找我,让我周六下午去文学院团委办公室找他谈点事。收到通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的那篇游后感搞砸了,我确实没怎么用心去弄那玩艺。我直接一口气写完了事,甚至连语法和错别字都懒得去检查。我在想如果他硬要让我重写的话,我就只能把罗叔卡博那篇《盒子变迁史》大修大改一下,多插入一些港澳旅行的见闻后将之重新鼓捣成一篇看起来特他妈冠冕堂皇的论文来交差。
周六下午我早早狠下心关了电脑,好好冲了个凉后把自己打扮得当。我在想自己如果跟平时在宿舍一样蓬头垢面地跑去见团委老师,估计他会强行让我转到艺术学院去。坦白说我对搞艺术的人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我总觉得他们连祖父那套装神弄鬼的做法都不如。尤其是那些搞艺术的唯物主义者,我在想既然他们信仰的是唯物主义那他们的艺术到底是以研究吃饭为主呢还是以研究打炮为主?在唯物的世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吃饭和打炮更重要的事。
我神清气爽地走在校道上,差不多是第一次察觉到道路两旁的大王椰子树居然像两堵墙一样高大结实,走在其中让人有一种仿佛自己的身份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错觉。路上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女生对我另眼相看,仿佛她们平日里对其它男生的青睐暧昧完全是少不更事时的幼稚冲动。我一下子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起来。为什么不呢?我二十岁不到,外貌俊朗,一米七五的个子。就一般的文科生而言也算是博览群书,如若真想要吹牛调侃也完全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无聊的太监宫女们逗得大笑不止。更要命的是我还跟顾海学过写一些云遮雾拦的现代诗歌。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曾经有首诗――名字就不说了――被梅山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歌手聂农作曲后收入到他张最负盛名的专辑《梅山往事》之中。他那张以梅山方言为主要唱腔的专辑自发行以来一直风行整个梅山地区。尤其是里面那首《All you need is money》简直他妈的朗朗上口,一不留神男女老少随时就会在你耳边来上两句:All you need is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第五章/2)
团委办公室在文学院教学楼右侧那一排低矮的白色建筑之中,往左靠近S大的旧图书馆。由始至终我都没搞明白大学里的团委老师到底是在负责何等事务,若以个人印象而言,便是诸如东厂或者锦衣卫之流的神秘机构。
等我赶到团委办公室时那个上次在澳门半夜还跟赵子才打得火热的女生刚好从里面出来,看她的脸色估计她上次去港澳旅游时因忙着拍拖所以论文全然没写出半点跟港澳有关的东西来。恩,估计她通篇都在写怎样打炮或者是避免被打炮,而自己却还浑然不觉。
“嗨,美女,里面什么情况?是不是很危险。”不管怎么说也算是老乡,正面碰到后我下意识地跟她打了个招呼。
“惨得很!搞什么鬼嘛,既然是基金会赞助的免费旅游怎么还会要求写这么严格的论文!早知道论文要求这么高我宁愿不参加这个鬼活动了,害得我自己在香港买东西都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生活费!”她一脸的愠色,看来情况的确不太乐观。“不过你倒好啦,还得了团委老师的表扬,他说你的论点非常有新意!”
“不是吧!”我听到后连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确实惊讶,我发誓。“我可没把那玩艺当回事,怎么会被表扬呢?是不是搞错了?”
“哪里会搞错,你叫唐德,是吧?”
“是呀。”
“那就对了嘛!你不知道刚才王老师发了多大的火呢,我前面两三个同学都被他臭骂了一顿。有个家伙跟他争执了几句,差点被他记过了说还要上报学校。什么逻辑嘛!”
“不是吧,这么夸张!他发什么火呢?”因为我听到团委办公室里面还有别的学生正在谈话,所以我就干脆拉着她打听一下情况。“按理这种论文跟本学期的功课不相干才对呀!况且他应该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是内陆省份的学生,本来对港澳地区就不甚了解,就这么走马观花地逛一下能写出什么有干货的论文来呢,是吧?”
“就是嘛,至于吗!……对了,好像你也是湖南人吧?”她突然问起我的籍贯,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恩,不过这回她看我的神情确实跟上回去港澳旅游时不太一样,至少不会再像路过街边的地摊货时极不情愿地用眼角余光毫无兴致地一扫而过。
“对,我是湖南梅山人。你呢?”
“梅山!我怎么没听过?我是长沙人!”她说长沙人时特意加了点长沙话的腔调,带着种仿佛只有长沙人才是正宗的湖南人的自豪感。长沙人就是这点让人恼火,搞得好像湖南就只有长沙这么一个地方。
“长沙,那蛮不错。”我信口恭维了一句,但马上我又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恭维她,于是接着来了句,“岳麓山风水还不错,是块埋人的好地方!”
“岳麓山?哪跟哪呢,岳麓山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外地人一提到长沙就只知道岳麓山,其实根本不是哪么回事。长沙好玩的地方多着呢,岳麓山算不得什么!”她喋喋不休地说道,仿佛岳麓山是她们家后院一块不值一提的荒山一样。
“是嘛?可能吧。”我附和了一下,准备就此结束谈话。坦白说我觉得长沙除了岳麓山,确实没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了。顾海以前跟我说要找时间专门去一趟岳麓山,拜谒一下山上的亡灵。我们已经差不多约好了大一寒假就去,我不想跟她就岳麓山再生出什么别的枝节,省得扫了旅游的兴致。
就在这时刚才在团委办公室里谈事的学生走了出来,也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原来是叶子才。这时我才明白刚才这女的怎么会一直呆在这跟我闲扯个没完,原来她在等这小子。想必他俩已经处一块了,我估摸。果然他俩手牵着手并肩走了。差不多快要下楼梯时,那女的突然回头冲我喊了句,“嗨,老乡!我叫林秋宜,你回梅山要是路过长沙的话记得一定要找我玩哦!”
我听后朝她哦了一声。我心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我觉得如果她没有男朋友,如果她男朋友此刻没在场,那么她在仅仅跟我交谈了一次后根本就不会主动告诉我她的名字,也不会邀请我路过长沙时找她玩――哪怕仅仅是出于客套。这当然说不出什么原因,但我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自打湖南卫视那些综艺选秀类节目持续火爆以来,貌似一夜之间所有的女孩都学会了非得把自己搞成一副炙手可热的派头。这个可怕的趋势已经愈演愈烈了,我发誓。
(第五章/3)
我走进团委老师办公室,这还是我头一回跟文学院的团委老师打交道。开学那会当然也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需要跟团委接触,但大多只是蜻蜓点水罢了。我只知道团委老师姓王,是个三十不到的潮州人。他从北方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回S大工作到现在,不温不火,一直待在团委老师的位置上。
进去后我顾自找了个跟他办公桌相对的椅子坐下,以非常含蓄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办公室。不管怎么说,就团委老师的身份而言他办公室的书籍还算是蛮多的,而且并非所有的书籍都是什么马什么列的理论书籍。甚至有那么一两本是小说,甚至。
“你是湖南梅山人?”他边收拾手头的文件边问我。
“对,很偏远的一个地方。”我如实答道。
“听说那里几乎与世隔绝,至今依然巫风盛行?”他仿佛对梅山颇有兴趣似的说道,“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梅山风土人情的介绍资料,感觉那是个蛮奇特的地方。”
“与世隔绝倒还谈不上,不过确实很偏远。至于巫风邪术什么的,我想主要也是因为人们的认知观念稍微有点落伍而已。不过现在跟外面都差不多了,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梅山年轻一代基本上也都是泛唯物主义者,很少有人还信之前装神弄鬼的那一套。”
“你刚才提到一个什么词来着?……泛唯物主义者。是你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吗?”
“差不多吧,是我的一个朋友自创的概念。大意就是指那些没有任何实质的信仰或者认知观念……只是简单接受了一些唯物主义泛泛而谈的粗浅结论,却因此而对其它信仰和形而上的东西都产生了恶性免疫的人。”我字斟句酌地答道。泛唯物主义是顾海以前跟我提到的一个说法,他曾说中国真正全面研习并信仰唯物主义的根本没几个人。他称那些不了解唯物主义却因唯物的缘由而反感其它信仰的人为泛唯物主义者。你和我,我们都是泛唯物主义者,结尾时顾海不无哀伤的说。
“恩,这个概念倒蛮有意思的。这么说你们――你和你那个朋友――有点反感唯物主义罗?”
“反感倒也谈不上,不过要说打心眼里喜欢它恐怕也难。就像有时候你去商场买一件你不得不买的东西,到了以后才发现所有这类商品都是同一种风格。倒也并非是很糟糕的风格,而且可能恰好相反,其实它是一种很时尚很得体也很实用的风格。可问题是当你完全没得选的时候,你总是提不起兴致。因为这玩艺你只要安心接受就行,根本不用动脑子。”我看他没有对这个话题反感或者动怒的迹象,就大概地说明了一下自己由来已久的想法。当然,其实这些主要是顾海的想法。
“恩,你的想法倒的确有点古怪。”说完他从自己的办公位置站起并走了出来。他在我面前踱着来踱去,仿佛在分析我刚才的言论似的不时微微点头或摇头。“那么唯物主义之外,你还对什么哲学感兴趣?――先喝杯水吧!”说完他转身朝我示意,用手指了指门口的饮水机。
“王老师,坦白说我对任何这类博大精深的认知体系都感到疲惫!”倒了一杯水后我象征性地边啜饮着水边继续说。“因为中学时我们一直很难有足够的闲暇来应对它们。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精力来应对,要么你只是得到一些装点门面的空洞概念和论断,要么就会被它们牵着鼻子走上一段弯路,说不定掉进坑里都不知道。”
“――OK,我们言归正传吧!”他好像突然失去了耐心。我承认我是有点绕舌了。每当有人想跟我谈点什么深刻的东西时我总免不了会绕舌,因为我心里没底。
(第五章/4)
“这次你港澳旅游的论文写得还不错,除了部分错别字和句法问题外,其它的我觉得都还不错。我建议你拿回去再修改一下细节,可能在后继一些相关的活动上我会安排将它刊布出来。对了,买椟还珠的那个提法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恩,算是吧。以前看过的一些文章当然也给了一定的启发。”我小心翼翼地应对着,我还不确定他是不是也读过罗叔卡博那篇《盒子变迁史》。当然啦,我的论文大体上都是自己写的,除了核心部分借用了他那个买椟还珠的比喻来画龙点睛外。
“如果能破除户籍限制,人们可自由迁徙、自由地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发展安家并获得完全一致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你觉得这是一切改革的核心所在,且不论上层建筑盖的是民主的新瓦还是传统的茅草。”他自言自语式地念着我的论文的结尾,“恩,不过我想你这些结论还只是些不太成熟的构想。”他转头望了望我。“但总比他们那些照抄照搬的东西要强很多。我简直受不了那帮人,连抄都抄得那么明显,搞得好像我什么书都没读过一样。”
我听了并未应答。我又开始思考上午看到的某个百家乐投式的的可行性了。我对那些民主体制或者政治改革什么的根本就不感兴趣,况且我这篇论文只是一时兴起之作,并没指望它还真能开出什么奇花结出什么妙果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论文其实跟这次港澳之行不怎么相干。如果你没参加这次的活动照样也得写出跟这差不多的东西来。难道这次旅游没有任何让你触动和感兴趣的东西?”
“倒真没遇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美女一个也没认识,连搭讪的都没有。”我笑着敷衍道。我决定不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赌场之行,哪怕对方也是赌鬼。
“哦,那有没有去逛一下澳门赌场,听说很豪华很气派哦,而且里面还有免费的饮食呢。去见识一下倒也不错!”
“这个还真没!”我有点紧张地说谎道。“我对那些东西向来不感兴趣,尤其是像斗地主打麻将什么的,纯粹是浪费时间。”
“那好吧。”他听后兴趣索然。我突然间觉得他也是个赌鬼,我真担心刚才要是跟他坦白自己的赌场之行他说不定会马上拉着我一起分析某个投注法的优劣。我几乎能判定他也是一个百家乐玩家,后来关于他的各种传言证明了这一点――但当时他显然不可能主动提起这个。
“今天找你来其实也就这些事。论文你拿回去把细节再润色一下,下周三之前交回给我。――对了,有一种叫百家乐的博彩游戏,你知道吗?”他突然掉转话题问我。
“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我斩钉截铁地答道,然后离开了团委办公室。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意图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玩百家乐。何况他还是团委老师――体制内的人你永远无法用常理去揣摩。
(第五章/5)
后来毕业那年他跟我们一起离开了S大,他移民澳洲了。据坊间的说法他在澳门总共赢了差不多一千万。但同时也流传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讲法,说他输了几十万公款后跑去澳洲投靠了他的一个舅舅。以前我一直觉得锦衣卫或者东厂之类的机构都是些卧虎藏龙的地方,事实果真如此。
几年后在深圳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又听人说起过他。一个本科毕业后去墨尔本大学读研的同学说曾经在悉尼的赌场见过他。那小子也算是个半吊子富二代吧,留学那会经常出入悉尼和墨尔本的赌场酒店,把他老爷子大半辈子挣到的钱财都败了个精光,最后文凭也没拿到就被勒令提前回国了。他后来在深圳一家通讯公司做海外销售,经常往返于南美和非洲等地卖贩各种看起来还不错的山寨手机。飞来飞去的间隙里他会在深圳偶作停留,于是跟我们几个同学小聚了一下。那天在KTV里他喝得有点高了,玩骰子时老是输给一个那会已经当妈的女同学。后来他没玩了,站起来唱了首歌Beyond的《海阔天空》,然后拉着我有一阵没一阵地瞎侃了一顿。他知道我也在玩百家乐。他问我输了多少,我信口说了个数。他叫我最好趁早收手,他说人这一辈子免不了要跌倒。关键是怎么爬起来!他有点亢奋地拍着我的肩膀。我知道那几年他做海外销售挣了不少钱,他爸妈也原谅了他。但那会我玩百家乐正进入到一个微妙的境地,突如其来的几次大输让我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一败涂地,但同时习惯性的赢钱让我又觉得不仅能回本说不定还能因此而获得一定的财务自由。那会我正跟朋友合伙操盘一家转型做APP的手机SP公司。所以我就把话题扯到智能手机上了,那是2012年,刚好是国产智能机将要起量的当口。他没接我的话芷,突然提到老王――就是在S大时我们的团委老师――他又发达了,他在悉尼的星港城见过他。我有点困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加个又字。
“这么说当初老王确实是在澳门赢了一千万才移民去澳门的罗?”我反问道。
当时那个事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那情形就好像中学晚自习时突然停电了然后大伙有点幸灾乐祸地提前下课回宿舍就寝时在半路上手舞足蹈说个没完的那种沸沸扬扬。
“倒没传闻的那么夸张!”他否决道。
那同学说他那次刚好输了个精光闲着没事就在赌场瞎转悠,见到老王后就蹭了他一顿饭并聊了好一会。
“你知道老王是怎么赢到钱的吗?”他反问我。
我摇摇头。我有点好奇,我确实不知道。大学那会我跟团委老师,确切地说是跟所有的老师都没什么沟通,也没打听过他们的私事,更不知道他们到底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我耳边压低声音细谈起来。看他叙述时的那股兴奋劲我觉得这小子的赌瘾还没完全消除。他早晚还会再赌的,我心想。
(第五章/6)
老王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刚开始在澳门其实只赢了点小钱,一开始也只是玩玩而已。后来他舅舅一家都移民澳洲了,他就总琢磨着也移民出去。也许他已经腻烦了那一切,团委老师什么的。但他越是急着想要赢钱移民却输得越多,结果没几下就把自己七八年存的小几十万都输了个精光。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插手接管了文学院的一笔活动经费,大概有六七十万吧。那会他已经没什么耐心了,干脆就铤而走险破罐破摔。他想办法把这笔钱挪了出来拿去赌。而且那会他心里有个念头,不管是输完了还是大赢一笔他都移民走人完事。大不了输光偷渡去投靠他舅舅――偷渡出境对潮汕人和闽南人都不是难事,他们有那个渠道。这么一来因为他完全没什么压力加上把把都是玩命的节奏,结果真被他碰到好牌路一次赢大发了。十五个庄十个闲,一靴牌赢了八九百万。
“反正总数确实超过了一千万,”说完那哥们提了提裤子或者说只是做了个提裤子的动作。他的裤子没什么问题,他喝得有点高了。
“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该加那个又字,”最后我淡淡地应道,“照你这么说的话老王总共就大赢了那一次。”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哪怕一次也好。靠,一千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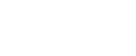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