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宿命论
“宿命就像万有引力,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你想要逃离它的掌控时却发现自己的双脚永远无法离开地面三尺。”
――罗叔卡博《宿命的万有引力》
我初次踏进澳门D场时,依然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泛唯物主义者,悲观惶恐,心无所依。那会我刚上大学,突然觉得生活没了方向,干什么都没意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专业,也有热心的学长提醒我说要多参加社团活动,甚至还有人跟我提到过什么职业规划,告诫我上大学时要拿到一些有用的证书,比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驾照什么的。但这些东西归根到底只是些幌子,到头来我真正伸手想拿的是什么我心里完全没底。就像有时候我们去逛商场时心里明白要买点方便面、香皂、内裤和纸巾什么的,因为这些都是马上要用得着的。但同时你又觉得这些玩艺其实可有可无,可买可不买,这些只是你被动需要的东西,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快乐和安慰。真正能打动你的东西,这个商场里头却一件也没有――我刚上大学那会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话虽如此,但我又不得不上大学,因为我哥没上大学。从小到大我哥样样都比我强,处处打压我。他个头高大魁梧、性情通达、处事干练,除了功课平平外简直无懈可击。所以我只能抓住这唯一救命的稻草,好歹找回点尊严。问题是在哥哥的影响下我爸甚至我们整个家族大多数人都认为读书根本没什么屁用。他们能随口说出一万个例子来证明读书无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能挣到钱,这是他们最终的说法。当我哥中专毕业后去到深圳跟一伙同样中学都没怎么念完的人一起捣鼓山寨手机而发了横财后,我们那个家族甚至整个梅山地区都开始大肆流行读书无用论了。所以当我考上大学准备远行念书时,我差不多是在众人的唉声叹气中离开了梅山。坦白说有时候我也觉得读书确实没什么用,又是背单词又是记公式,还有各个文言虚词的用法等等。你甚至连好好跟女生搭个讪打个炮的时间都没有。那种日子过得有点像沙漠里的干尸,反正有滋有味光彩照人的好果子一个也没结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想着自己总得在某个地方强过我哥才行,更何况性格有点内向的我那会除了读书实在找不出别的事可干。我骨子里向往着一种无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填志愿那会想都没想就报考了南方最偏远的大学,广东的S大,彻底远离了梅山和它乌七八糟的一切。我没有去北方仅仅是因为我怕冷。我喜欢南方的漫漫长夏,贪恋夕阳下那些仿佛没有尽头的黄昏。
(第二章/2)
所以我读大学纯粹是出于惯性――高中念完了就继续念大学,如此而已。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是真心喜欢读书的,比如顾海。对他那样的人而言读书就像吃饭穿衣一样重要。
顾海是我的中学同学,高中三年我们都在同一个班,而且一直同桌。认识顾海后,我才完全脱离祖父那个装神弄鬼的世界。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顾海是我认识的读书最多的人。他在中学时就读完了所有他认为值得一读的国产书。所谓国产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人写的书。说起来惭愧,像《文心雕龙》和《贞观政要》之类的玩艺,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去读,而且也读不懂。顾海是个极度内向的人,他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说话。高一我刚开始和他同桌时一度以为他是个哑巴或者弱智。可他一旦开口说话却能一口气跟你讲清楚李存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那怕你是个成天琢磨着跟刚好上没两天的女朋友打炮的学渣也会对中国几千年幽暗曲折的历史来点兴趣。事情是这样的,高一语文课讲《伶官传序》时,老师问大伙有没有谁对李存勖父子的生平有所了解,如果谁知道的话就请举手讲一讲。那老师问了两三遍没一个人举手,看他那神情似乎很失望,仿佛如果没人站起来跟他互动一下那他这堂课就根本没法往下讲了一样。最后顾海站起来说他知道一点。于是他就开讲了,滔滔不绝。我当时惊讶得不行,要知道他跟我同桌一两个月讲的话还没超过五句。顾海讲了有差不多十来分钟了,讲得倒非常流利,但对李存勖父子却只字未提,只在一个劲地讲唐末黄巢起义,还有那个叫什么鬼朱温的,反正是个叛徒。我心想这小子虽然不是个哑巴,难不成是个弱智。不过语文老师倒听得十分入迷,仿佛很多猛料他也是头一回听到。顾海讲了差不多整整一节课还没把李存勖父子的陈年往事讲完。顾海的口吻有点悲天怜人的意味,跟《伶官传序》里面欧阳修那种正儿八经打官腔教育人的口吻极不协调,所以老师在紧要关头打断了他。中学语文老师都是这副德性,他们希望你对文史类的东西感兴趣以便他们能更顺利完成授课的公事,但同时他们又不希望你们对真正的文史了解太多,他们怕你会因此而产生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想法。他们希望你将来也跟他们一样徒有其表,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了。
不过打那以后我对顾海倒是刮目相看,我几乎成了他的门徒。顾海家藏书丰富,五花八门至少比当时梅山一中那个破图书馆要有意思得多。在中学的图书馆,你甚至连一本原滋原味的书都找不到,都是些什么教辅题海,要么就是些被改写过的丛书或者是隔靴搔痒的评论性书籍――这些东西就好比一堆被人嚼过一遍后吐出来的残渣败壳。有一段时间我周末都不回家而是待在顾海家一起看书,扯淡。当你读书不是为了有用时,也就不会在乎那些什么鬼读书无用论了。
(第二章/3)
在我潜心在顾海家读书的日子里,我慢慢察觉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发现梅山地区的历代行政长官都跟顾海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的可追溯到宋代,那会梅山刚刚被中央王朝征服,民风初步开化。我是在顾海家的藏书的章印上发现这些的。甚至建国后在十年文革的动乱时期,梅山地区的文革组长也是顾海曾祖父的亲弟弟。当然话又说回来,梅山地区原本就只有顾、唐、田三大主要的姓氏。顾姓是随宋代军官迁徙而来,唐姓是梅山本地人,田姓则是梅山归化后山上的苗族去草归田而来。既然梅山的州府官吏一直是由顾氏一脉垄断,那么这些行政官员之间沾亲带故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梅山历代最高行政官员都是顾海家的直系亲属,仿佛有一种神秘的世袭制在梅山地区连绵不绝。
有一次我跟顾海提起这个事,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想不到你小子还是个实打实的官二代,真他妈的深藏功与名呀。他说这是一个宿命,就像遗传病一样世代相传、永不绝断。
“那么以后你小子不是梅山的县委书记就是梅山的县长罗?”我反问他。
“那倒不一定,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完全没那个想法。”顾海掩上书后诚恳地答道,“我不是当官的料,我堂弟倒是有那个天赋。”
顾海的堂弟叫顾铭,比我们小两三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你都不会觉得他比你小。说起来奇怪,哪怕是比他大五到十岁的人,他们一同站在那里,你甚至都无法断定他比别人小。他正是那样一种人,在他们十五六岁时就俱备了一个稳重而诚恳的面孔,此后的几十年他们都能保持这个面孔的体面与威严,永远都是那样一副不容置疑的表情。顾铭也像那些天生的领袖一样,既能在适当时机鼓动人心,又能让自己的同伴死心塌地。他上高一的时候就当上了梅山一中的学生会主席,而正常情况这个职位都是由高二的学生来担任的――高三的学生则要忙于应对高考。据顾海所言,那小子甚至打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要知道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南人,我到现在都还分不清以F和H开头的发音。
(第二章/4)
也许顾海说得对,这真的是一种宿命。就像梅山的官吏由顾姓世袭一样,梅山的神巫历来都由我们唐姓垄断,代代相传。而DB对我们家族来说,也像是一种遗传病。
说起来我们家族还真的有种遗传病,是隔代相传的那种。我祖父右手有六个指头,我也有六个指头,不过是左手。在梅山地区有个奇怪的说法,右主巫,左主赌,意思是说右手司通灵祭祀之职,左手司赌钱博命之事。梅山历代神巫的标志就是右手长有六个指头。人们都说因为神巫是梅山地区至高无上的荣耀,所以出神巫的家族隔代就会生出一个左手长六个指头的赌鬼,以之作为神巫以凡人之躯来侍奉神灵的代价。所以我们家族每隔几代就会出一个神巫,同时也必定会出一个赌鬼。在我们老家当谁打牌输钱输得很离谱时他就会换左手来抓牌,美其名曰神仙怕左手。这一说法正也源于此。
所以当我刚一出生时,我父亲和我哥哥就一直疏远我,他们对左手长着六个指头的我怀着一种略带恐惧的憎恨。我母亲当然是爱我的,虽然她也是从小听着梅山的各种传说长大,但我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她对我的疼爱里头带着一种隐晦的负罪感,仿佛我所承担的罪恶之中也有她的一份。当父亲在家时,她对我的关爱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甚至只能刻意冷淡。所以我童年时除了跟祖父厮混,实在没有别的搞头――其它小孩因为被他们父母教唆,一个个都对我敬而远之。于是我就只能跟着祖父成天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梅山的各个村镇。也许就在那时候,祖父作为神巫那种不事稼穑成天自由浪迹于乡间地头的生活就深深感染并影响了我,此后我的一生都在追逐他那种自由自在的影子。
而我作为D徒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追逐这种自由而一路扬起的灰尘罢了。
(第二章/5)
多年以后当我冒冒失失一脚踏进澳门D场时,我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宿命在我身上起了反应。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神奇――整个人异常地兴奋同时又异常地清醒。而且我们的意识仿佛生出另一个自我在旁边看着此刻的自己并提醒说,多么神奇,将来你一定会记住眼下这不同寻常的一刻。于是我下意识地抬起了自己的左手,那只附在大拇指边上多余的发育畸形的手指突然微微抖动了一下,仿佛它也在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平时这个手指很少动,因为发育不良这个指头的反应十分迟缓,平时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以前我自己也像看待异物一样看待它,直到此刻我才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原来它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想就算大一那年我没有误打误撞进入澳门D场,DB这个宿命依然会以其它方式在别的地方将我掳获。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事物感到极度兴奋和沉迷,比如考试。几乎很少有人像我那样几近变态般地沉迷于考试,仿佛每次考试都是一个节日那样,而且规格越高难度越大的考试就越能让我过足瘾。每当考试来临哪怕当时我正在感冒或者肠胃不适也会立马恢复到战斗状态。看着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仿佛如临大敌,看着老师小心翼翼地拆开密封的试卷,看着整洁而又略带油墨气味的试卷像一个丛林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升华到一个更超然更神奇的高度,仿佛我的人生的确赋予了某种神圣的使命。
奇怪的是对于其它那些略带技巧性的DB,比如斗地主,跑得快,麻将,跑胡子等等,我却完全提不起兴趣。我觉得那些只不过是尘世间一种攻于心计的肤浅游戏,为了赢几个仔或者少输几个仔而苦于算计,步步为营。
(第二章/6)
在更上一层的法则上契合命运的反复无常的唯有BJL。它仿佛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衣服一样,一旦穿上就和我本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所以哪怕是当我输得精光连吃碗方便面坐趟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当房东宁可不要尚未结清的房租也要像赶老鼠一样将我赶出去时,我对BJL依然没有半点怨恨。我恨的只是自己。我恨我自己不能看透BJL幻化万千的表象和它始终如一的本质――人生中看似神圣庄严的起伏成败在绝大程度上其实都只不过是庄闲永恒的随机波动罢了。很多时候我们赶着向上的波动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而获得成功,这并非我们自身的品质或者能力所使然。同样当我们身处向下的波动时不管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往往都无法扭转失败的局面。所以后来当我听到人们以一种非常郑重其事的口吻谈论自己或者别人的成功时,我总是忍不住想笑――他们所讨论的极可能是跟他们自身品质和能力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他们却把这些随机而出的结果看成是自己人生最主要的成就和价值。好比你成天在跟人骄傲地谈论说什么十年前狮子座的流星雨如此绚丽从而让你带给当时的女友过了一个多么难忘的生日既而你未来的岳父送了套北京三环内的房子给她当嫁妆然后这套房子几年来涨得有多么离谱而你也因此迈入成功人士的圈子生活优渥,如此云云。其实你跟那些仅仅因为没带女孩看十年前那场流星雨而至今光棍的吊丝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你恰巧搭上了房价暴涨这一波大行情罢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房市,股票,贵金属,P2P,各种买进卖出的生意,甚至包括创业的时机等等。当那些行情结束时总有人无法舍弃曾经的成就与荣光,妄图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挽回颓势却发现自己竟如此柔弱不堪一击。他们始终都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赢得糊涂,输得冤枉。
这是BJL最终教会我的无数道理之一。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所有人的宿命相差不会太大,差别大的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罗叔卡博曾说,宇宙本身只是一出随机生成的喜剧,而整个人类历史只不过其中一个小小的玩笑。想到这一点,难道你还会对人生中种种趋势(振荡)和机会(噪音)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而耿耿于怀吗?
对我而言这个玩笑的核心就是BJL。它一点一点向我展示出宇宙的真相,也让我认清自己。每一个风平浪静的表象后面都有一个令人疯狂的真相。
上帝是个老D徒,他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掷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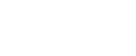




最新评论